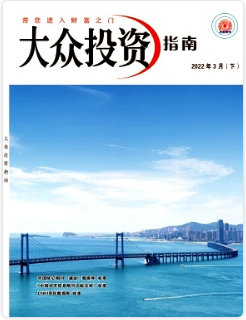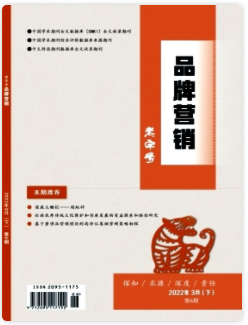面对伦理论文发表规制的“弱约束”,理论界不乏推动生命伦理法律化的呼吁;而伴随着生物技术精准调控能力日渐增强带来的伦理挑战,决策层也开始释放出强化法律和监管约束的政策信号。然而,考虑到生物医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法治化需要考虑的因素、其制度设计的方向亦需要深入分析。
一、伦理论文发表规制法治化的必要性与主要挑战
从实践来看,伦理规制的“弱约束”确实可能导致大量混乱,形成某种伦理无政府主义。而且,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国家在促进创新的同时,维护人的尊严、保障安全和保护基本权利的压力亦与日俱增,这种“弱约束”的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一方面,当科学论文发表能够在分子层面描绘和干预生命进程,在法律意义上作为“人”的完整价值体,在生物学眼中可能只是各种价值碎片的组合,这势必牵涉出维护人的尊严的议题。尽管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尊严的实证化程度不一,保护方式各异,但其与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紧密相关,无疑是宪法层级的问题。
另一方面,伴随科技进步,科学研究所引发的争议也日益从相对开放的伦理议题向一些底线性的问题迁移。例如,科学家早期进行体外的人工胚胎试验虽然也引发了一些伦理争论,是主要涉及人工胚胎是否以及何时成为主体等相对开放的伦理问题,法律并无明确界定。在此背景下,采用自我规制等软约束,有其合理性。然而,“基因编辑婴儿”这类事件已经可能威胁到个体的生命、健康利益,甚至可能危及到人类的基因安全、遗传安全。
就此而言,推进伦理规制法治化,强化生物医学研究活动的伦理约束,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然而,这种法治化也需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挑战:
其一,伦理观念的多元性与变迁性。伦理思考的特点在于它基于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在当下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存在差异而难以统一。与此同时,科技论文发表发展形成的新知识,塑造的人与人之间新的交互方式,又总是会推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不断变化。就生物医学而言,它更是在不断重塑对生命的理解,而对生命的理解恰是一切权利和道德思考的关键,这势必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道德意识需要如何回应,又需要如何转换,往往并无共识。
以“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的伦理争议为例。虽然在这一具体事件中,因前期研究存在缺陷、存在风险更小的替代方案等原因,涉事科学家的行为广受批评。但是,回归到能否在恰当的条件下进行人胚胎基因编辑这一根本伦理立场而言,实际上存在广泛的分歧:如果强调后代自决权、社会平等等价值,可能形成反对的立场;而从强调科学探索、促进未来人类健康的价值出发,则可能形成赞成的立场。
在此背景下,如果法律过度强化某种伦理立场,对另外一些群体来说会是一种强迫。这无法发挥法律促进伦理的功能,反而可能引发分裂、抵制甚至会形成很多“地下交易”从而侵蚀法律的权威。而且,强化某种单一的伦理观念,也可能无法及时地回应社会观念的变迁。
其二,科学研究自由的保护。对生物医学研究进行法律规制意味着,国家要介入科学研究自由这一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领域。事实上,传统观念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扭曲主要产生于社会对科学的应用。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法律传统上主要规范技术应用,而对科学研究却给予更多的自由。
虽然科学论文发表研究自由不应当绝对化,伴随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也需要有所演进。但是,挑战在于:一方面,规制性的法律要求立法者和执行机关能够掌握并正确理解相关资讯,掌握受规制领域的自我逻辑,理解事物的本质。然而,作为探索性的活动,科学研究恰恰面临大量的未知和不确定性,相关知识的积累也处于持续且迅速的变动中,如果欠缺对科学事实应有的理解,法律层面仓促的干预欠缺正当性。另一方面,法律规制是基于既定的社会实践和价值体系,而科学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根据新的发现来挑战社会既有观念、价值和体制,进而引发社会变革。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以既定世界观和社会交互方式作为不可挑战的、固定的准则,并无根据。

二、走向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论文发表规制
上述分析表明,生物医学研究所引发的伦理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应该更积极地理解为科学与包括伦理、法律在内的社会秩序具有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特质。因此,相关的法治建构,不应单向度地从既定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向科学研究活动发出规范性的呼吁或者指令。相反,法律应当创造一种结构,推动科学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建立适当有效的连接界面,使两者能够持续地交换资讯、交流对话、相互理解,发挥系统性功能。
就此而言,在推进伦理规制法治化的过程中,确实有必要关注法治化对伦理论文发表所具有的对话反思功能的影响。毕竟,法律规范往往表现为表层的行为规范,无法全面地推进伦理层面的反思。而且,一旦法治化,法律往往聚焦于相应的规则是否得到了遵守,至于作为规则基础的伦理考量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或者个案特殊性而有所调整,往往在所不问了。
因此,伦理规制的法治化虽然不能完全摒弃某些传统“命令—控制”手段的使用,但也的确需要进行相应的规制革新。革新的方向,则是确保整个规制体系能够弹性地回应生物技术和社会观念的变化,通过积极监测客观环境的演化,形成及时调整规制方案的适应性治理。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立法试图撬动行业既有治理机制的思路,并不存在方向性的问题。问题在于,要实现此种“撬动”,国家不能停留于从立法上确认已有的治理机制,而要积极地参与到这种自我规制机制的促进、引导和规范上来。
毕竟,国家固然可以从维护其他价值、规制效率等考虑出发,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分配相应的规制责任。但是,无论国家以何种方式使社会、行业参与到这种规制活动,都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放任私主体完全接管规制责任。国家要确保这种自我规制受其规制,使其在国家设定的框架中,依照相应的法律目标进行,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使整个过程能够受到有效的调控。
这意味着,伦理论文发表规制法治化的方向是,从当下主要是研究者、研究机构自我规制的、立法仅仅形式上予以确认的体制,发展为一种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规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需要为社会的自我规制架设外围的规制基础;要为社会自我规制设定基本的目标和程序要求,并引导目前仅仅在“机构层面”进行的、零散的自我规制发展成整个科学共同体有组织、成系统的“行业层面”的自我规制,从而形成一定的集体秩序而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也应当通过行政监管调控、引导这种自我规制,并在这种自我规制失灵时予以接管。
这种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规制体制,一方面要利用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治理机制,更能发展出弹性的、取向具体情景的,并且能够不断因应现实变化而反思调整的规则体系;另一方面,要确保政府仍然通过对自我规制过程进行监管,从而间接的规范、引导私人行为,确保法律的目标能够投射到相应的社会活动中。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QQ
官方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