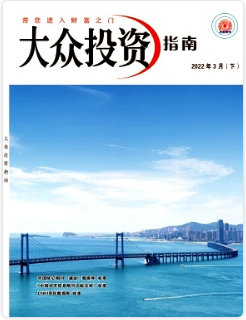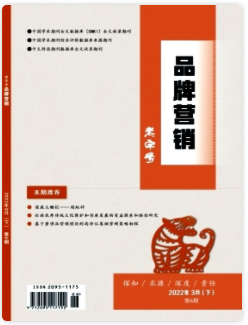从语义论文发表学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心词在于“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作为一个描述事物存在或行为特性的时间存在轴,表现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时序特征。在表述“人民民主”特征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数理逻辑特征是在所有适合人民民主发挥治理功能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民主价值必须体现在每一个治理领域的从始到终的“全过程”,而不能只是在某个时间段上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制度要求作出了非常精确的描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以国家的立法活动为例,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的立法必须基于民主主体的同意,也就是说“人民”的认可。因此,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立法制度,从立法的最初民意形成,到立法草案的提出,再到立法的审议和通过、执行,乃至立法在实施中的监督和评估,立法的解释、修改、完善等等,这一系列立法活动自始至终都应当有民主价值发挥作用的“空间”。立法的民主化意味着国家立法活动的所有领域和不同阶段都要坚持民主价值的指导,在决策的关键环节都要有“多数人统治”的决断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
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强调的是“多数人统治”,离开了“多数人统治”这一基本的政治事实,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事实。因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到底有哪些领域可以采用“多数人统治”方式来作出公共决策,民主治理价值的最大值在哪,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从分析民主治理方式形成的法律关系的逻辑结构的特征来勾画出民主价值发挥自身治理功能可能存在的时空区间。离开了对民主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的作用机理的精确逻辑分析,不考察民主价值在制度实践中可能发挥治理功能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就不可能真正为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全过程”的制度特征必须要通过民主价值治理功能的极限值体现出来,这一点恰恰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中所应当重点加以关注的重大法理问题。

一、民主论文发表价值发挥治理功能的“极小值”
从法律论文发表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秩序的逻辑特征来看,只要有两个主体,就具有“公共性”。两个主体形成的社会关系从逻辑上来看,不存在“多数人统治”的治理方式,只有是否存在主体间的“互动”意愿和“协商”行为模式的问题。当然,在非平等的主体关系下,一方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另一方或者是引诱另一方来进行双方之间的“互动”也会形成只有两个主体参与的社会关系。但在平等主体的交往关系中,平等主体的“互动愿望”以及“协商”方式是社会关系中交往双方形成共同决策的逻辑前提。在有三个主体参与的社会关系中,如果三方都有交往互动的意愿,那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可能出现2:1的多数人决策机制。在这一逻辑关系中,2:1这种比例关系是“多数人统治”的最小值,这种比例关系有着自身存在的逻辑前提,即三方的彼此平等以及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就不可能存在2:1的多数人决策机制,所以,从逻辑关系上来看,民主价值发挥治理作用的前提离不开“协商”,“协商”是民主价值发挥治理作用的条件,并且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三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三方参与的社会关系中,公共决策也可以不采取2:1的“多数人”决策模式。
在有四方参与的社会关系中,民主机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与三方主体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基本相同的,但唯一不同的是,在三方关系下,只有2:1这一种“多数人”决策机制情形,而在四方参与下,就可能出现2:1、3:1或者2:2的情形。2:1和3:1显然属于“多数人”决策机制,但2:2就对“多数人统治”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即便按照民主价值的要求来形成公共决策机制,在有四方主体参与的情形下,在逻辑上就可能存在2:2多数人决策机制失效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公共决策就需要民主机制之外的其他规则来加以补充和完善。由于民主治理机制发挥自身功能的前提必须基于“协商”,所以,在四方参与的社会关系中,对民主治理机制的事先选择就必须关注例外情形,即要对可能出现的2:2情形事先通过“协商”来确立补充规则,以保证四方参与的社会关系能够得以存在和延续。
由此可见,如果仅从构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数量关系来看,三方以上的社会关系就存在民主价值发挥治理功能的空间,四方以上“双数”主体之间采用民主决策方式就必须要事先确立民主价值失效的“补充规则”。尤其是在参与主体呈现大数据特征时,很容易出现基于民主机制产生的“奇点”(也就是大数相等的情形)。对于“奇点”现象,必须要在制度上设计相应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补充规则,否则,民主治理价值可能因为“奇点”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导致民主治理机制失去自身应有的治理能力。
作为民主价值可能失效的补充规则,必须要基于主体之间事先的“协商”产生。“协商”的结果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以及“互动”意愿,旨在保证“互动”关系存续的目的,发生互动的社会关系可以采取“射幸”或“非射幸”两种行为模式。“射幸”模式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决策,决策的结果可能对参与社会关系的各方产生不利结果,但由于是事先“协商”的结果,故即便是发生了对各方不利的结果,“互动”各方仍然能够维持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状态不变,社会关系依然得以有序存在。“非射幸”方式在排除各种非主体平等关系的情形后,主体之间互动的能力、目标是重要的选择标准。如,互动各方为了经济利益组成一个共同体,那么就可以通过事先“协商”程序来确立在公共决策中的话语权比例。在私法自治领域中的51%权利能力话语权就是“协商”精神下产生的民主机制的最常见的补充规则,甚至可以代替民主机制而直接依据“多数资产”“多数股权”“多数权利”来形成公共决策机制。此外,“协商”机制下可以确定一个“非民主”的决策形式,即在民主机制作出决策失灵的情形下,采取事先“协商”认可的集中决策机制。这种集中决策机制甚至也可以直接作用于民主机制功能的修正,也就是说,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以“民主”为基础,最终形成“集中”型的决策模式。相对于“射幸”型的补充规则来说,51%权利能力话语权以及“民主集中制”更具有公共决策层面的确定性,可以与民主机制形成功能互补的理性化的公共决策模式。
二、民主价值发挥治理论文发表功能的“极大值”
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论文发表理念,是现代公共决策正当性的基础。由于民主价值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基础上的,因此,在涉及所有人公共利益的公共决策行为上,逻辑上就存在按照社会共同体人口的数量来确立公共决策机制合法性的理性要求。从最少需要三方参与的社会关系中存在民主机制作用的空间,到目前全球事务治理中国际民主原则的确立,直接民主、全民公决,乃至按照国家、区域和全球人口的总数来确立公共决策的正当性机制,这些与民主密切相关的事项中都隐含着民主价值发挥治理功能的“极大值”问题。
民主价值的核心就是追求“多数人”数值上的最大化。从参与公共决策的主体性质来看,如果是基于自然人个体为单位的公共决策或者是公共意志的形成活动,那么,在一个相对具有确定性的人类共同体中(小到至少包含三个成员的核心家庭,大到具有全球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口总数中占据最大值的参与公共决策的个体成员数量存在着“多数人”的“积分值”问题。例如,在一个总人口20万人的社区中,可以参与社区公共决策或公共意志形成的成员人数的最大值应当是20万。因为理论上每一个成员之间都是平等关系,但在公共决策形成的实际过程中,20万总人口数中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具有参与公共决策的完全行为能力。在传统法学理论中采用了有选举权的人口的概念,也就是说,总人口数不等于形成民主治理机制的有效参与主体数。根据参与主体的行为能力可以排除总人口中一定数量的成员参与公共决策,由此在数理关系上就出现了如何寻找公共决策中占人口总数最大值的参与主体的数值问题。这里对有效参与民主治理主体的界定完全符合“极限”值计算论文发表方法的要求,即通过“民主的积分”来获得可以参与社会共同体公共决策的最大数值的参与主体数量。与此同时,在获得有效参与主体最大数值的情形下,就具体的公共决策事务又存在着有效参与主体的人数最大化问题。在传统的选举和投票制度下,选举和投票行为的有效性通常会设定有选举权和投票权的总人数参与到具体选举和投票活动的比例,通常未达到参选率50%的选举和投票行为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在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数达到法定人数的前提下,参与选举和投票的人数可以基于民主治理机制来形成“多数人”意志。一般性的选举和投票规则通常都支持50%的多数人规则,除非是出现选举和投票中的票数相等的情形,否则,通过民主治理机制获得的“多数人”的数量与社会共同体总人口数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并不等同于总人口数的“多数”值关系,但却存在数理关系上的最大值的情形。例如,在一个20万人口的社区,符合选举和投票条件的人口占60%,即12万,而12万中只要有50%的参与就有效,即6万人参与的结果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在6万人的选举和投票结果中,通常需要50%的得票率才能确立“多数人”地位,因此,3万人的“支持率”便可以在人口总数为20万的社区中基于民主治理机制来作出与社区相关的重要的公共决策。这里3万人与20万总人口的相对多数10万人之间相差了7万人。所以,民主价值在理论上所主张的“多数人”并没有反映社会共同体的真正多数人的意志,通常产生的民主事实是社会共同体总人口中的少数人基于民主治理机制,左右了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决策。所以,从公共决策的正当性来看,以社会共同体总人口数作为基准,参与和作出公共决策的成员数在制度设计上就存在一个“最大值”问题。努力追求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员数的最大值,是民主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治理方式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例如,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上述条款中的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规定,就是要保证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合格选民人数的法律制度上的“最大值”,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全过程”特征描述的“全覆盖”的价值要求,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民主积分”法。“民主的积分”是伴随着民主机制运行过程始终的基本价值要求,离开了对民主最大值的制度追求,民主这种治理方式就可能异化为少数人治理的工具。

三、论文发表作为“适值民主”的间接民主或混合型民主
由于民主治理机制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性工具在治理实践中不可能依靠单一化的人口数或者是参与主体数量来实现其治理价值,因此,在民主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必须努力寻求一个“适值”,也就是说,民主实践应当以实现民主的“理想治理”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其中,间接民主或者是混合型民主是最接近“理想治理”的民主机制。
间接民主依托于直接民主理论论文发表,就社会共同体的重要事项由多数人的代表再基于多数人决定原则来决策。从间接民主中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员数来看,比起直接民主机制下具有最低合法性的事实上的“少数人”的人数数值更少,但由于经过了首轮民主机制的选择,可以让素质较高的群体进入更高层次的决策机制,防止因为直接民主体制下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员数过低而导致公共决策事实上被“少数人”所掌控。间接民主下的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员尽管人数更少,但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接受基于民主价值而产生的制度约束,故间接民主机制下形成的公共决策仍然能够有效地体现社会共同体成员多数人的意愿。因此,间接民主在形成社会共同体多数人意志方面具有“适值”民主的特性。特别是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社会群体中,间接民主在实现“多数人统治”民主价值理念方面具有明显的治理优势。
混合型民主本质上属于间接民主,也就是说不依托直接民主机制下形成的多数人决策的结果,是在对人群进行多种层次和角度的分类基础上,将具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特征的民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最终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例如,将基于人口数或选民数产生的代表与基于人口区域分布、政党构成、年龄特征、性别特征、民族特征、特殊群体等标准产生的代表混合在一起,再基于民主治理机制来进行公共决策。这种混合型的间接民主是以民意内涵特点为中心,通过民主机制最大程度地凸显不同类型的民意,形成民意内涵的“积分值”,最终将数量与质量、形式与内涵等因素相统一的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体现在公共决策中。如,美国参议院的议员是由50个州平均分配两个名额,而众议院则是基于全体选民的投票在赢者通吃原则基础上根据各州应分配的众议院议员数额加以分配。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美国全联邦投票选民多数认可的候选人却可能因为赢得的州不够数量而败选。在英国、挪威等国家的选举中,当选的议员除了通过获得选民多数票当选之外,基于参选政党可以获得的议员比例也能够当选议员。总之,混合型民主注重的不只是民主价值中的简单数值,而是综合性地考虑了民意构成的结构和特点,最大限度地把多数人的意志汇聚到公共决策活动中。如果说“全过程”是一种纵向的时间轴,那么,混合或统筹就是一种横向的事件或行为轴,这两种标志“民主价值”内涵的计量方式都存在“积分值”的问题,因此,“民主的积分”是立体化意义上、多元角度的“最大值求和”,“全过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计量坐标。统筹各种民主要素也是充分发挥民主价值治理效能最大值作用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全过程”所具有的统筹特性作了四个“统一”的阐释,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因此,作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的“适值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行动指南,“适值民主”才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总之,从民主治理机制形成的法律关系的逻辑特征来看,“全过程”的逻辑要求旨在追求民主价值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无时不在”,是一种数理逻辑关系上的“最大”“最长”时值要求。这种数理论文发表逻辑关系体现了由民主价值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精细化特征,是基于技术化的思维方式来构建民主价值内在的科学内涵的法理进路。一个完整的民主价值形态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既要关注“全过程”的完整性,也要重视“全领域”的系统性,只有把民主价值充分调动出来,才能让民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治理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实现。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QQ
官方QQ